专访巫鸿 | 学艺术,到底学什么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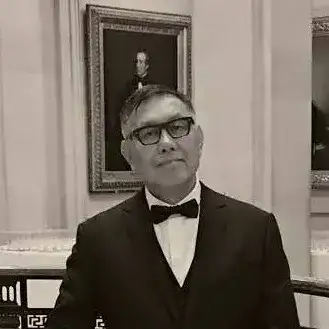
巫鸿
著名艺术史家,批评家;
策展人;
芝加哥大学教授;
哈佛大学终身教授;
美国国家文理学院终身院士;
著有《重屏: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》
《第一堂课》
《美术史十议》
《中国绘画中的“女性空间”》等

01
学艺术,到底学了能做什么?

毛思翩:现在很多年轻人热爱艺术,但是真正能选择艺术,不受家庭影响的比较少,您觉得到底艺术是什么?
巫鸿:我觉得现在大家的理解还跟原来差不多,好像艺术是一个比较虚的、比较接近玩的,不像是一个正事,这个理解在外国也是这样。一般而言,艺术好像是美术馆里的东西,就像音乐是舞台上的东西一样,这个理解虽然非常流行,但是实际上不太正确,而且非常的窄。
因为我们是训练学生做艺术的,所以我们知道学生并不是都搞这种艺术,一小部分人会真的变成艺术家,比如拉提琴就真的上台独奏,这是非常少的。很多人就是做和艺术有关的事情。
比如就像我原来是画画的,后来做了美术史,不是画画没用,画画还是底子。但还有很多做艺术的人,去做了建筑学、设计、计算机相关的事情,甚至有学美术的人做了法律,因为法律很多牵扯到艺术品进出口税,很多拍卖行都需要这样的法律人士。这类法律不懂艺术不成,所以现在美国的一些大的律所,要请艺术史家来看画。因为如果一个人要保险,这张画值一千万美元,还是值一千美元,他得请专家来鉴定,当然不是所有的律师都得变成艺术史家,但是他要有一定的修养,对他的专业很重要。
所以对艺术的看法可以宽一点,首先不是完全画画,一辈子就靠画,这种人是有的,但是很多人不完全是这样。很多学艺术的可以做很多和视觉有关系的东西,而视觉不光是艺术,不光是画画,很多周围的东西都是与视觉有关的,特别是现在计算机变得那么重要。
所以我觉得艺术确实不像理工科那么保险、那么实际,但是也不要马上把它想得那么悬,它也有很多很实际的东西。

02
美与美术的区别

毛思翩:艺术会牵扯到美,您是学艺术史的,您对美的理解是什么?
巫鸿:我觉得这里也有一个误解,我们有时候把美术和美学有点混,因为美学,实际上是哲学的一部分,它考虑的问题就是“什么是美”,这是从德国十七八世纪开始的一门学问,谈什么是美,有崇高的美、悲伤的美、漂亮的美,很多种美,这是一种思辨的东西。
美术虽然叫美术,它不是主要表现美,也不是整天画美,其实看一些艺术家,他真的在画美吗?不一定,他有时候画的是社会很悲伤、很黑暗、很让人不舒服的东西,所以把美术一下就连到美,就太快了,那就变成了月份牌、大美人,也变成艺术很小的一部分。

03
西方的基础教育

毛思翩:国外的教育跟国内可能不太一样的是,国外经常去美术馆,学生也有很多机会可以接触到音乐、美术,您觉得中西方的教育体制下,对人本身会产生什么影响?
巫鸿:西方的大学中我对美国大学比较熟,我是大学以后去的美国,一直在大学从事教育,也做过研究生,所以我觉得在大学的层面上,区别是蛮大的。
高中的层面上,开始区别也蛮大的。美国上中学是很松的,会看很多东西,但是到了接近大学的时候,压力也蛮大的,要上好大学也得通过很多考试,分数也要好。
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大学不太一样呢?
就是美国不是一下推你去搞一个专业。美国把专业化的长度拉长,不是一上大学就要有一个专业或两个专业,你可以多想一想,选了也还可以改,甚至大学毕业了还可以改。
欧洲不太一样,英国有点像中国,大概中国这一套是从欧洲来的,就是选一个专业会比较早,上大学就好像结婚似的,就和一个专业结婚了,美国上大学还可以不要结婚,还可以推一推。
推一推的好处就是让你打下一个人文或者思想的底子,即使你将来做律师,还是学过一些美术史、学过一些世界名著,大学的一些基本课程都是必须要学的。
打底子还有一个好处,就是一个人他有选择的权利,比如你干了一个专业不好,你可以换。即使大学毕业选做医生的,可能这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也能挣钱,但是有的人花了很多年学烦了,不想做了,他就能够去换一个专业,因为大学学了一些打底子的基础课。所以从这两个角度,我觉得美国的大学还是比较健全的。
04
我学美术史主要是爱研究人

毛思翩:您刚去美国的时候,中美差异还是特别大的,对您一定冲击挺大的?
巫鸿:我去美国的时候是八十年代,全世界都在发生变化,冷战结束,柏林墙也倒了,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,包括我在中国、在美国、在全世界,大家都能有那么一种希望,从我自己来看,我觉得就像进入一种非常自由,重新寻找自己前途的时代。
在经济上,我觉得其实挺好,因为在国内我算大学生毕业,一个月大概挣60来块人民币,在国内不算太糟,因为什么都很便宜,我当时的宿舍是在故宫里面,我记得我的月租是7毛钱一个月,加上水电费、吃,还是有二三十块钱剩下的。
到美国我完全是靠奖学金,因为是哈佛大学给我的钱很少,但是当时觉得很富,刚去的时候是四百美元,有个一人间的小宿舍,也没有什么太多愿意花的地方,所以经济上觉得非常高兴。
其他的就是一种自由,就是可以看所有的书,也没有压力,当时也不想工作,就是有机会去看书、去听讲、去学东西,这对我来说是非常让人兴奋的,特别是一些东西原来在国内听说过,但是没有机会学,比如人类学。
我最开始想学人类学,不是美术史,因为当时觉得人类学这个名字特别吸引我,因为我看了人类学的定义,就是研究人的,这个对我吸引力太大了,研究人的行为、人的思想,有那么一个学问研究人,因为当时在国内对人文主义、人本主义特别有兴趣,对于摆脱阶级,摆脱政治有一种人,大写的人。居然还有那么一个学问来研究人,所以非常兴奋,念了很多书也学了不少,但最后又回归到美术史。
但是再回到美术史,我就觉得我做的美术史很多就是关于人的,不是关于作品,后来别人问我,你做美术史有什么特点?我觉得首要的,美术史是人创造的,这是一个人的表达,所以这一点对我是非常必要的,这就和人类学有关系。
05
人人都是艺术家?

▲ 巫鸿策展《物尽其用》展出现场
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(MOMA)2009
毛思翩:现在有一种观点,说人人都是艺术家。还有人说没有艺术作品,只有艺术家,您是怎么看的?
巫鸿:我觉得这当然是很好的想法,人人都是艺术家,但是实际上是人人都可以变成艺术家。这不是糊里糊涂就已经是艺术家了,没有这事,就是人人都有这种潜能,甚至不一定需要训练就可以开始做艺术,那就是艺术家,但是没有这个思想,那还不是艺术家。
所以我觉得这是正确的,我和一个艺术家叫宋冬一起做过一个项目,后来我写了一本书,叫《物尽其用:老百姓的当代艺术》,这个项目我觉得非常有意思,因为他就是把他妈妈变成艺术家,他妈妈就是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,整天收点垃圾,就是物尽其用,收了很多很多。
整个过程我都参与了,他妈妈真的变成了一个艺术家,他妈妈和家里人也都一起布展。我就被任命做韩国光州双年展的主持,我就把这个作品放到那,成千上万“垃圾”一样的东西,后来那个展览,宋冬和他妈妈都得了大奖,所以他妈妈就变成一个艺术家了,还得了一个大奖章。
后来宋冬的艺术家朋友就开玩笑说,这不公平,我们干了一辈子,学了那么多艺术也没得奖,你妈妈刚做了一件,就得了金奖。宋冬很聪明,他说她就做了这一件,可是她是用一辈子做这一件作品,所以也很感人。
他妈妈去世后,这个展览也还在国外展,曾经还去过美国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,那是最重要的地方了。
但是我觉得他妈妈去世以后,这个作品的性质就有变化,因为他妈妈不在场,原来他妈妈总是坐在那里,观众就可以和她聊天,她总要给你讲故事,讲她这一双鞋是谁的鞋,是什么时候买的,为什么有那么多布头,她会给你讲很多故事,而且她脑子特别清楚,什么都记得。
所以这本书主要是他妈妈的故事,就是这个布头是在哪儿买的,西单的哪个布店,因为买不起布又特别喜欢布,就赶这一批布剪剩一点,她就把它买回家去了,所以最后就剩好多这种布头,很多故事非常有意思,这就是老百姓的艺术,或者人人都可以做艺术家。

06
美术,其实是视觉的科学
毛思翩:您研究美术史,是从什么角度去看呢?
巫鸿:不是完全从美的角度去看的,很多艺术不能说它美,比如很多现实主义的作品表现一种社会的阴暗,很难说漂亮的。当然佛教雕像有些很美,但是有些是有很崇高、有很宏大的气魄的。
我们的研究从社会思想的角度是一个很大的部分,也有很多别的部分。最基本的就是关于我们怎么看,关于眼睛能看见的东西,这个东西对一般的人来说就是看,它不是一种知识。
我们美术史要做的,就是教人看到这个东西,包括就一把椅子,它说明我们今天的文化思想,它可以是一个证据、一个知识来源,但是大部分人不太懂怎么做。
其实我们现在研究古代,我们发现一个墓里头有很多杯子、碗,然后我们想当时的文化、当时人的审美、当时的器物是什么样的,这些东西就需要一种能力,把看见的东西转化为描述,转化为一种思想可以拿出来让人知道。
所以这里面包括很多,包括趣味、宗教、文化,其实美术史要说大了就是关于视觉的科学,我觉得现在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很长的时期的尾部,就是还以为知识就是文字。
现在我们一想到什么是知识,马上就是书,书就是字。其实你想一想历史上人类的产物,大部分不是字,而是东西、建筑、城市、器物,各式各样视觉上的东西,这部分的研究还是很少的。
所以真要研究古代,很多书是很局限的,只是一些文人在那写,很多东西也不写,你想找的事也找不着。你得研究具体的,比如唐代城市什么样,书里就很简单,但是通过所谓的美术、考古,就能把它复原出来。
所以美术史这个词就是很耽误人,其实它不是关于美术或者美的术,是关于整个视觉的科学。

